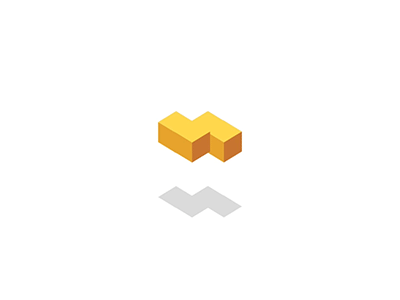“改土归流”还是“改土设流”
——1937年甘肃“博峪事变”再考察
王志通
杨氏家族的世袭土司集政、军、教、族权为一体,统治卓尼藏区达五百多年。1937年,第19代藏族土司兼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被内乱部队在博峪杀死,史称“博峪事变”。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地方实力派与藏族各界围绕事变善后相互博弈,甘肃省政府借机在形式上完成了改土归流,成立以卓尼设治局为中心的国家基层政权,但又保留了以杨复兴兄弟、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为中心的土司制度。这种形式上的改土归流实为“改土设流”、“土”“流”并置。
关键词:博峪事变 改土归流 卓尼设治局 改土设流
作者王志通,1989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邮编200433。

土司制度是历史上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的重要举措,“以本土之人,司本土之事”,即奉土著首领或当地酋豪为土司,授以官职,用“以夷制夷”的策略进行统治和管理。随着国家权力不断向少数民族地区延伸,中央政府逐步进行改土归流,即废除世袭土司改为中央政府派任流官,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本文所述的甘肃卓尼地区位处汉藏边界,自明代建立以杨氏家族为核心的土司制度后,其在数次改土归流中保存并延续,直到1937年突发的“博峪事变”,国民政府才着手进行“改土归流”。大部分地方通史类著作和文史资料对该事件有所介绍,但错讹较多且鲜有分析,学术界对卓尼改土归流的已有研究或“还原”事变细节、考述国民党政权处理事变的经过,或分析卓尼基层政治合法性重构时遭遇的困难,但他们在具体研究中忽视了偶发事变的内生因素、善后中对改土归流的商讨以及卓尼设治的具体情况,低估了政教合一制的根深蒂固,进而模糊了“改土归流”的实质所在。对此,笔者结合新近发现的档案资料,从卓尼改土归流的历史分析中,揭示以杨氏家族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土司制度在突发的“博峪事变”冲击下的裂变。军政、教权分离,司令部与设治局共存,完成了形式上的改土归流,而实为“改土设流”。
一、以卓尼土司为中心的政教合一制
卓尼土司先祖些地率部于明初抵达卓尼、迭部一带,扎稳脚跟并逐步确立了独特的统治模式。1418年,卓尼归入明朝统治版图,些地也因收抚迭部沟18族被授予洮州卫世袭指挥佥事兼武德将军,由此奠定了以些地家族为核心的世袭土司制度。以土司为中心的政教合一制度发端于此,兄受封土司,专管军政;弟承续僧纲,掌理宗教。在传袭过程中,“土司长子例袭土司,次子例袭僧纲。遇独子时,土司得兼管僧纲,政教合而为一”。1508年,明武宗朱厚照以杨洪一名赐第5代土司旺秀得,卓尼土司遂以杨为姓。入清后,土司制度承袭下来,杨土司为清效命,多立军功,受封品级逐渐升高,管辖地域不断扩大,成为“甘青各土司中实力最强者”。1902年,杨积庆继任为第19代土司兼摄禅定寺僧纲,并延至“博峪事变”爆发。杨土司集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等诸权于一身,即使政教两权在形式上分属,但实权终掌于杨氏家族之手。
世俗权力以土司衙门为中心。土司的对外文稿由1名延聘于内地的红笔师爷主办,其对内文稿的起草和誊写等则由房科负责,房科内设掌案1人、经书2人、帖书2人和文书4人,他们皆由土司直接领导。土司衙门内设3名总管:大总管总理衙门内外一切事务;二总管理钱粮和土司家族的祠堂家谱;三总管掌理伙房和磨房。衙门正门处设炮手1人,在土司因公出入时鸣炮三声兼打五更。此外,设两名头目掌管行政改土归流,其下设传号4名,轮流在传达室值班,及时将内外事务传达土司。传号之下设2名班头直管监牢。杨土司辖区分48旗,其中23旗派有旗长,其他诸旗则由总管掌理。旗长负责征收钱粮,遇战事则领兵出征,遇重大案件则奉土司之命持票传人。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人员均选自内掌尕,三总管、两头目、传号和旗长皆为土司悬牌任免,其他勤务人员则多由大总管选拔。
各旗由旗长、总管、头目来管理,他们在其所辖部落享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统治权,对外是部落的总代表,对外是部落的总指挥。他们管理和分配所属草场、草山、土地等资源,向部落内属民征税。他们依例以习惯法调解部落内纠纷及命盗案件。当发生对外纠纷时,他们作为部落代表出面商议;如发生对外冲突或战争时,他们则率领部落武装参战。部落成员“不能借故逃避”,“必须随时绝对服从于部落的利益,绝不能有丝毫损害部落利益的行为,更不能背叛部落”。可见,普通民众与头目、总管、旗长、土司构成了一种迭次累进的强有力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土司衙门为中心的政治系统管辖着该地的世俗社会,而宗教领域和精神世界则以禅定寺为核心的藏传佛教系统为宗。

宗教权力以禅定寺为中心。禅定寺是卓尼地区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藏传佛教寺院,1710年康熙帝赐“禅定寺”寺名,沿用至今。僧纲、大法台与尚书楼共同构成寺院最高的权力中心。僧纲衙门为寺内最高行政机构,设1名大秘书负责公私文件,多由天文历算学院的主持僧干巴兼任。大法台是宗教领袖,总领全寺宗教活动及相关事务,下设大格贵、总诵经师、聂巴、吉哇和格贵贤巴各1人,分管所属四扎仓的经典学习、教规戒律执行、重大佛寺活动安排和日常教务活动等。尚书楼主要由大格贵、吉哇和17奥昂(相当于教区)的僧人代表组成,以集体会议形式协商、管理并监督寺院各项事务。僧纲是禅定寺最高统治者,集寺院的行政、经济和宗教等各权于一体,即使不兼任大法台,也由代表僧纲权威和利益的大德高僧担任,僧纲自始至终、或隐或显地主宰着卓尼的宗教世界和精神领域。僧纲并非似活佛一样转世,或由前任土司次子担任,或由土司兼任。值得注意的是,在20代土司中,专职僧纲仅6位,其余皆由土司兼任,这更体现了政教合一的特点。
以卓尼土司为中心的政教合一制实质是以政权为主,“政治权威要大于宗教权威,政权大于教权”,“以教辅政,以政挟教,用宗教和文化纽带把辖区属民紧紧连在一起”。总而言之,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形成了世代赓衍的权势,加强了属民的凝聚力及其在政教上对土司的依附性。政教权力粘合在一起,在延续中进一步巩固,得以存在五百多年。这种神权统治形态下的政权统摄教权的模式常被成为“卓尼模式”,卓尼也因此在整个藏区和内地都享有盛名。特殊的卓尼模式在清以来的数次改土归流大潮中幸存下来,然而1937年偶然发生的“博峪事变”则有力地冲击了这一土司制度,预示着以卓尼为核心的政教合一制开始走向瓦解。
二、“博峪事变”及对实行“改土归流”的商议
1937年8月25日,杨积庆部二团长姬从周和秘书方秉义假称奉省府主席贺耀祖及鲁大昌之命发动政变,遂召集营长何建奎、安国瑞、王换英,副官主任李富才,警卫连长郑秉钧,骑兵连长金钟南,手枪队长曹彦寿,排长曹世虎、牛齐、杜佐堂等组成倒杨联盟,部署曹世虎、杜佐堂分率鲁大昌部窦得海所属20余人各架一挺轻机枪对准杨积庆卧室窗口和堂屋门,其余各人则分别负责杀死杨积庆家属、一团长杨英和副官赵希云。当晚,他们依计行事,冲入位于博峪的土司官邸,杨积庆乘乱逃至山神林水磨附近;杨的长子杨琨夫妇、孙女等5人当场毙命;而前往捕杀赵希云的金钟南因与之交情甚笃,赵得以幸脱。姬从周得知后,领兵三路在山神林展开搜索,杨积庆在离阳坡磨房中误认是部属正在寻找自己,便主动出来迎见,结果被哗变部队用乱石打死。这次事变发生在卓尼博峪村的土司驻地,故史称“博峪事变”。
次日,姬从周、方秉义等人在博峪召开会议,列出杨积庆“背叛党国、勾结外患、中饱赈款、私售国土、虐待百姓、破坏教育”等几大罪状,宣布成立“卓尼维持委员会”,姬从周为主席兼代洮岷路保安司令,方秉义等十二人为委员,并广贴标语,发出通电。得知事成的鲁大昌随即电告甘肃省政府,引姬从周等言“(杨积庆)密派代表,勾通日满,背叛党国,扰我抗日后防”,表示时时防范。28日,姬等人向省府报告,称“窃查甘肃卓尼世袭土司兼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本系专制余孽、封建游魂,独以赋性阴狠险诈,暴戾恣俎,黑暗专制,铁蹄压榨,无所不用其极。又复野心勃勃,图谋不轨,假服从政府之名,行背叛党国之实,种种罪恶,笔难罄述……职部全体职员等为保全整个国家前途计,为挽救西北边疆危机计,为解除切肤痛苦并求本身生存计,誓难与背叛党国之专制土司并立共存,但一发千钧,迫不急待,民众等以光明意志,凭纯正心田,本良心驱使,应事实迫求,已于本月寝日以军事手段做最后制裁。”同时派人把守洮河沿岸各桥渡,封锁交通和通讯,“严密保护防地治安”,让卓尼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等候上级处理。
正值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全面抗战正酣,此次位于大后方的突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刚代理甘肃省主席才两个多月的贺耀祖一面报告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一面要求鲁大昌随时电告事变起因、现实情形及民众态度,并妥慎防范。其他各种势力纷述意见或建议,如与卓尼相邻的临潭县长薛达称“自该司令部成立后,杨氏所属形成特区”,建议政府“应趁此改土归流,筹设设治局。”鲁大昌认同薛达建议,认为卓尼“为甘青锁钥,接壤川边,应有设治必要。番民痛该土司之压迫积怨已久,亟思求治”,并反复电请省府“改土归流”。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调查后报省府称:“民众对于此种谋逆行为殊抱不满,委以委员会名义继续统治,诚恐难以维持。”虽然贺耀祖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等都认为应借此机会对卓尼实行改土归流,筹备设治局以为设立新县政府之过渡,逐步瓦解根深蒂固的政教合一体系,但这仍需查明所有详情方可定论。8月30日,省府第516次省务会议决定派国民党中执委委员、甘肃省政府委员田崐山亲往彻查处理。
“博峪事变”虽发生仓促,“事变之前未闻若何征兆”,但这实为内外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黄正清等人认为此次事变纯系该部少数职员挟嫌报复,“杨司令对部下诚有刻薄情事,或行罚过当,难免怀怨”。黄之言撇开了来自鲁大昌的外部因素,意指杨本人未能有效统驭部属,处事缺乏公正,赏罚尚欠分明。事实上,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内部相互倾轧斗争,杨积庆重用三团长杨英和副官赵希云,对他们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之举从不责罚,多次包庇容忍,一团长郝应隆、二团长姬从周对后者深为不满,内部纷争愈演愈烈。此外,性情直率、作战英勇的姬从周对杨早有怨恨之心。1935年初,杨令姬从迭部曹儿沟给驻于四川秋吉一带的胡宗南部送粮运盐,由南向北旅行的范长江正好碰见,对姬派人艰苦送粮有所描述。见到送粮藏民甚多,“有用牦牛载粮,有用背负者,背负者比牛载者为多”。姬从周的诚恳之举深得胡赏识,欲委任其为“前线剿匪司令”。杨积庆对胡宗南热心拉拢姬的行为甚为不悦,对姬严加训斥。姬因此记恨于心,对杨的命令多行敷衍。一次,杨派姬去迭部出差,姬托词家中有事。杨当众骂姬“整天在家当倒出(当地土话,意为与近亲搞男女关系的人——笔者注),何以为人?不服从命令,何以率众?”另一方面,曾在土司衙门从事的方秉义“因奸拐某故健将之子媳”被控告,杨调查核实后欲予以严惩。方趁机逃往省垣,积极策划倒杨行动,一边劝说鲁大昌极力襄赞,一边召集和联合对杨深为不满的姬从周、何建章等人,组成利益联盟,密谋推翻杨的统治。由此,“博峪事变”爆发,土司杨积庆及其家属数人被害。这种由少数人发起的变乱虽能终结土司本人的性命,但土司家族存在的影响深厚久远,服膺杨氏统治的势力依然强大。
杨被杀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忠于杨土司的杨景华等人在禅定寺发出鸡毛信,调集北山诸旗、车巴诸旗、朱扎七旗藏兵欲报仇雪恨。北山总承官麻周带领精壮悍兵两百多名开赴卓尼,云集洮河两岸。同时,田崐山、贾大均等人抵达临潭后发现,实情并非如薛、姬等人所报的“一切安谧如常”,而是暗流涌动。多数藏民并不认同姬等人的行为,对其求援“多以大逆弃之”,且“番兵越积越多,情事悲愤,其一致口号为惩凶拥杨”。9月12日,麻周等率兵反攻,姬部溃散崩离,几番交战后,姬被毙身亡,除方秉义等少数人逃亡外,余部均缴械投降,存在近20日的临时维持委员会随之瓦解。
虽然卓尼乱局初定,但如何重新分配该地的权力引发了纷争。鲁大昌、薛达等仍坚持迅筹改土归流,贺耀祖、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及南京国民政府以同意的口吻安抚鲁、薛等人,另则等待田崐山的调查详情,再行定夺。深谙藏地边情的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认为“边民智识简陋,世袭统治印象亦深”,“维杨氏册封已有十八世之久,年深代远,颇具根底,一般民众确有诚挚信仰”,杨积庆“诸子尚幼,不能治理一切,拟请由四十八旗推举素有声望、于军政教三者足能措置,且为人民所信仰者一人,假以名义,使其暂为维持,以杜异念而固边防”。为稳定局面计,黄正清认为应暂由杨氏家族掌握统治之权,再视成效、舆情、民众之依归等循序渐进式“改善设施”。换言之,黄正清认为“博峪事变”造成的形势不足以全面开展改土归流。卓尼及周边藏民代表向田崐山、贺耀祖等人致电,“要求一致愿奉杨氏次子为领袖,除此任何人绝不拥护,并有散投新主之表示”。可见,此时观点有四:一为立即改土归流,为鲁、薛所议;一为视调查结果再定,为省府所持;一为暂缓改土归流,为黄所议;一为保留土司权力,为藏民所呼。
田崐山听取当地知识阶层、藏民头目意见后,提出解决办法,既保留代表和行使土司权力的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又新设卓尼设治局。即实行“改土归流,卓尼设治局长由省政府委派”,“洮岷路保安司令一职因全番信仰所系,迫于事实,非以杨积庆次子复兴暂代不可,因其年幼,拟设副司令一人,由设治局长兼代,参谋长一人由全番公推历史悠久、声望素优之杨一俊充任,以资佐理,其团长等职由该司令另案请委。”贺耀祖批准了田崐山的解决办法。第522次省务会议决定“改土归流”,成立卓尼设治局。其辖境区域辽阔、部落杂处,符合设治局组织条例的规定,其名称与他省也无重复,于1939年4月29日在国民政府正式备案。同时,省政府任命杨复兴为“洮岷路保安司令”,杨丹珠则被国民政府封为“禅定寺辅教普觉禅师丹珠呼图克图”。
可见,最后的意见是在遵循各级政府原则下,对鲁、薛、黄等人观点与当地民众的意见折中。将看似对立的两种变革体制的方式加以糅合,在“改土归流”的“改”字上做足文章,将取消土司制度的路径转换成部分保留,将直接设立流官制度进行管理的方式嫁接到土司统治地域上。这种结合构成一种新的变体,即土司制度的变体与国家县级政权的实体同时存在。
三、卓尼设治与“土”“流”并存
因卓尼处于拉卜楞保安司令部与165师势力范围之间,故“局长由省府委派与黄、鲁无关干员充任”,并兼任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以此享有军政权力,不致杨复兴等人独掌大权。最后决定由临潭县长薛达暂行兼代卓尼设治局局长。9月22日,就职仪式在田崐山、甘肃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胡受谦和保安四团团长吉猛等人亲自主持下于禅定寺进行。虽然鲁大昌与临潭马仁山等人对此非常不满,但国民政府借“博峪事变”之机完成了形式上的“改土归流”。成立设治局已为定然,但对卓尼有效地控制和管理,防止地方社会重现乱局是省府的初衷。卓尼内部矛盾依然存在,来自周边势力的影响同样很大,鲁大昌所派军队在一旁虎视眈眈。新成立的设治局要想在重重乱象中站稳脚跟着实不易,来自上级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对政府而言,乱局中建立的设治局是对卓尼进行改土归流的重要举措,它的存在有利于后续行政工作的开展,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加强对藏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省府给予设治局有力支持,赋予设治局长调兵权,可“酌予组织自卫武力,强化施政力量”,同时积极完成设治局建制。
第一,办公等经费的确定与办公场所的修建。衙署是国家政权机构得以存在的重要体现,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旧址遭兵燹被毁,前司令杨积庆虽有所修缮,但房屋仍不敷使用,故首任局长薛达从省府请准拨得2千大洋开办费和1千元杂费作为办公基础费用。该局日常经费则依康乐和肃北设治局标准定为每月1千元。而正式办公衙署放弃博峪而选定于绾毂全区的卓尼柳林镇,并着手另行新修。薛达将“博峪事变”首犯姬从周位在卓尼城内的房产擅自充公,“改修衙署,就所领开办费项下购置木料、兴公建筑”。次任局长吴景敖认为将姬产充公既不合法,也违背宽大为怀、团结民族之深意改土归流,并暂将设治局办公机构设于禅定寺旁的宋堪布住所,请准设治局关防,且在未到之际暂借用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关防代替。吴景敖又虑及姬从周房产地理位置优良,加上薛达已拨发开办费购置木料,动工修建,故可先将地产发还,然后依法按地价征收后改建衙署,略作变通而不致多耗财力。该局会同地方权势人物与姬从周侄子反复磋商,最后以国币2百元典得姬从周房产30年,期满再行换契展限。由此,修建衙署的争论历时一年方才告一段落。该局正式办公后,下设民政、财政和教育3科,及合作指导和警佐2室,各科室有科长或主任1人,科员1-2人、办事员1-2人、雇员1-2人不等。
第二,划定界域,绘具图说。界域是行政主体管辖的行政区域,它意味着行使权力的地理范围。1932年,省府令杨土司会同临潭县长刘炎划界绘图。卓尼生、熟番及其他部落杂处其间,连杨积庆对辖境亦不甚明了。故杨从中阻挠,勘界划线的议案遂被搁置。“博峪事变”后卓尼设治,划界绘图再次提上日程。卓尼土司辖地广漠,插花地甚多,又无地方文献可资详考,局长会同藏族上层人士和当地权贵历经艰难,最终勘定界域。为行政管理方便,将原属临潭的双岔、西仓、木多、牙贯等地归卓尼,将卓尼所属喇嘛岩等四十庄酌归临潭。由此,该局辖境“东南接岷县、西固、文县,南接四川松潘,均仍旧界,西以西仓与青海同仁及夏河属叠藏据才知界为界,西北以西仓、双岔及临潭、卓尼与夏河之旧界为界,东北以卓尼与康乐、和政治旧界为界,东南除大部利用临潭、卓尼旧界外,其由临潭划归卓尼之走廊地带之东线,即以左占川河下游之中心线为界”,面积共约3.5万平方公里。
第三,制定设治计划。吴景敖上任后详细考察地方情形和社会状况,制定了《卓尼设治纲领》,并逐步付诸实施,“以坚边民向化之心,免其复萌观望之念,而蹈夏河设治徒具虚名之覆辙。”设治纲领共分为12部分:1.划界;2.设治地点;3.政制之改建;4.户籍钱粮之交割;5.拓殖之步骤;6.交通之改善;7.自卫组织之建立;8.保安部队之整理;9.民族关系之调整;10.教育之推广;11.民族健康与防疫;12.行政机构及经费。纲领主要集中于削弱土司和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的影响、增强自身实力及筹办社会事宜三点。一、在削弱旧势力方面,设治局逐渐从保安司令部收回行政权力,分步设区长;改总管、土官为联保主任和甲长等;废除乌拉制度;裁减草头税;紧缩保安部队员额并调整其人事。二、在增强自身实力方面,设治局掌管辖区户籍;重新厘定征税科则和年征钱粮数;引资成立公营贸易公司;开发林木和矿产资源;改善卓尼交通通讯状况;成立自卫组织。三、在筹办社会事宜方面,设治局通过共事、通婚等法改善民族关系;整理木筏教育捐;兴建僧俗学校;医治流行病等。
经吴景敖、刘修月、丁剑纯等几任局长励精图治,各项行政措施次第推建,粗具端倪。但这并非如明驼所观察“卓尼事变后,杨氏政令不畅,统治范围日趋缩小,由过去平均长度四百里渐缩至百里以内,乃至三数十里不等”。虽然不彻底的改土归流和建立国家基层政权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土”“流”并存,相互博弈。因强势的旧势力对抗新权力的渗透和扩张,以致设治局筹建衙署、划定界域等基本工作都无法缺少服膺杨土司家族的地方权势人物的参与,该局的政令也只能在城郊附近勉强行使。数年后,设治局的政令仅能达于洮河南北沿岸的村落,上下迭部、黑番四旗等地仍在杨司令的直接统治之下。即使设治局政令达于地方,也须“借重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的力量才能做通”。如设治局对保安部队的改革止步不前,在辖境内推行保甲制度在插岗地区遇到十分强大的阻力。所以在1943年,无论是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胡受谦还是卓尼设治局长刘修月都认为“现时卓尼改县尚未达成熟期,乞审慎考虑”,且省府会议数次都未能通过“改局升县”的议案。直到1949年后,卓尼设治局才与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一同湮没在历史洪流之中,完成了“改土归流”。
四、结语
杨氏先祖从明初至卓尼逐步建立了以土司为中心的政教合一制,集政、经、教和族权于一身,统治着卓尼藏区的僧俗世界。卓尼土司制度根深蒂固,延续五百年之久,但在1937年偶发的“博峪事变”后政教体系开始崩解。姬从周、方秉义等人在与土司有宿怨的鲁大昌襄助下杀死第19代土司杨积庆,建立卓尼临时维持会,以图推翻杨氏家族的统治,但很快就被杨氏追随者率藏兵打败。国民政府据田崐山的调查结果,融合黄、鲁等各方意见,任命杨复兴为洮岷路保安司令,成立卓尼设治局,任命局长并兼副司令,完成了形式上的改土归流。可这里的“改土归流”是土官在改,流官同设。废除土官、权归流官意义上的改土归流并不彻底,而仅流于形式,实为“改土设流”、“土”“流”并存。
设治局建成新衙署,大致划定界域、绘具地图,制定《卓尼设治纲领》,以图削旧立新,加强国家政治权力的渗透。然而,卓尼军政、宗教大权仍掌于杨氏家族手中,藏民仍视杨复兴兄弟为军、政、教权之领袖,省局政令仍仰司令部方能有效施行。虽然形式上的改土归流能将国家权力的触角延伸到少数民族地区,逐步松动和瓦解卓尼的政教合一体系,达成从旧到新的彻底变革,但传统势力依然深厚强大,顽固抗御来自国家政治权力的积极扩张。
综上可见,1937-1949年的12年中,代表旧势力的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与代表新势力的卓尼设治局共存。形式上的改土归流变成了“土”未废除而“流”已建立,“土”“流”共存,新旧势力同在,即形式上改土归流等同于“改土设流”。学者对土司制度变革的研究多将当地统治秩序的转变纳入区域社会变革中,将中央政府对土司权力的限制和改变均纳入“改土归流”中,目前学界对1937年卓尼“博峪事变”也视同“改土归流”。本文通过对“博峪事变”再考察,卓尼的“改土设流”被误作“改土归流”,进而忽视了地域社会变革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变革中存在的或隐或显的动力机制缺乏区分。卓尼此次的“改土设流”尤其特殊,它既不同于明朝在贵州的“军政分管,土流并治”,也不同于清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将土官直接改为流官,仅在官僚体制内进行的名称转换和自我调整,而是土官后代仍承享先辈所属权力,从外地调任的流官与之共有。笔者对“博峪事变”的个案研究意在提醒学界应当对“改土归流”详加区分,“改土设流”是“改土归流”的历史过程的过渡形式,也是易被忽视而不应忽视的内容。“改土归流”绝非废除土司、设立流官几字所能囊括,权力的真正“归属”流官往往存有一个十分漫长和艰难的历程,或隐或显地持续数十年,甚或更久。只有如此,方可更易理解土司家族的后续命运。
(该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文字有改动,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