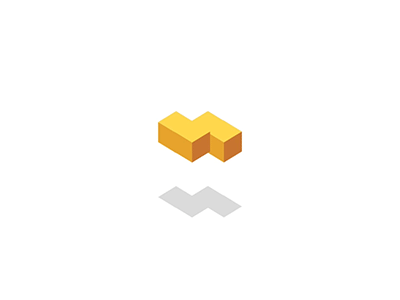第三章 汉乐府民歌
“乐府”本是古代掌握音乐的官署机构,六朝时,人们把合乐的歌辞、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成的诗歌统称为“乐府”,于是乐府演变成为一种诗体名称。沿用到后世,涵义进一步扩大,如宋人把词,元、明人把散曲也称作乐府。设立乐府机构的记载,最早见于秦代,汉初承之。当时的乐府只管民间俗乐,祭祀的雅乐则属太乐掌管。汉武帝时重建乐府机构,扩大其规模。其职能除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填写歌辞、编配乐器进行演奏外,还负有采集民歌的使命,始形成雅乐俗乐并存的局面。当时采集民歌的目的,不独为了观察民情,供朝会、祭祀等典礼之用,也有愉悦耳目的作用,更有满足自己“大一统”心理的动机。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收集、整理和保存民歌的作用。
汉乐府诗歌包括文人乐府和乐府民歌,现仅存百余首,主要保存在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中。民歌是其精华,现仅存四十多首,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辞、鼓吹曲辞和杂曲歌辞中,其中多数是东汉作品。
第一节 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达了汉代民众的心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汉乐府民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表现民众的悲苦、怨恨与反抗。汉代数百年间,豪族日富,黎民百姓日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妇病行》是反映这一内容的典型作品。诗中描写病妇托孤、丈夫乞求、孤儿啼索母抱的情景,惨绝人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孤儿行》则反映了私有制下道德沦丧导致的一幕悲剧。孤儿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父母在时,他“乘坚车,驾驷马”。父母死后,他成了兄嫂的私奴,备受虐待,长年被驱使外出行商,回来又被使唤去办饭、视马、汲水、养蚕、收瓜。如此辛劳,却“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他痛不欲生,“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这不只是一个家庭悲剧,还是严重的社会悲剧。《东门行》则表现了百姓困不可忍之后的反抗。诗写了一个城市贫民,面临生活绝境,被迫铤而走险的情景。诗中的男主人公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出东门,却又转回,再看家徒四壁,无食无衣,难以活命,于是决计“拔剑东门去”。妻子用天道和人情劝阻,也全然不顾,毅然走上反抗道路。这种对剥削压迫的自发反抗,正是汉代“群盗并起,国之将亡”的预兆。这类民歌汉乐府民歌,远超先秦民歌“怨刺”的界限,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
控诉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是汉乐府民歌的又一重要内容。汉代对外战争频繁,统治者利用战争对百姓进行超限度地奴役,百姓深受其害,他们以诗歌表现了强烈的反战情绪。如《战城南》,通过对激战后凄凉恐怖的战场的描写和人乌间惊心动魄对话,反映了战争给人民生命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对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有力控诉了穷兵黩武者的罪行。《十五从军征》更通过一位老兵回乡后目睹的悲惨情景表现了这一点。他十五从征,八十才得返家,六十五年的兵役,使他备受苦难,而归来后,早已家破人亡,亲戚丧尽,只有累累荒冢和断壁残垣,盼望已久的归梦被现实击得粉碎。
战争而外,又有赋税、徭役、灾荒、土地兼并,迫使人们离乡背井,漂泊异地,于是产生了行役者的悲歌。如《艳歌行》写一家“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受尽屈辱,发出“远行不如归”的悲叹。《悲歌》反映了异乡漂泊者“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的痛苦。这类诗歌,格调悲凉,催人泪下。
汉乐府民歌有很多作品反映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这一永恒主题,并藉之歌颂了当时人们追求的坚贞爱情和他们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与《诗经》时代相比,汉代男女青年在爱情婚姻上受礼教的压抑更重,但从现存作品看,其时人们表达爱情情感的浓烈程度,并不逊于《诗经》,而且更具悲剧色彩。如《有所思》写一女子思念远方情人,本想赠以珍贵礼品,却“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但这种深挚的感情,并不易断绝。她的一举一动,又害怕外人知道,内心充满矛盾。与此相类者又有《上邪》,女主人公向自己的所爱发出爱情誓言:“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以必无之事为誓,语辞铿锵,感情真挚浓烈,非爱之至深者不能道。
在表现爱情婚姻问题的汉乐府民歌中,弃妇诗是较突出的一类。《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是其中的代表。前者写的是因丈夫喜新厌旧而爱驰的弃妇,最具普遍性。诗通过对话,真实表现了弃妇的委屈心理和故夫后悔、恋旧的复杂心态。弃妇温顺、柔情的性格正是在汉代儒学影响下形成的新的人物性格。与此不同,《孔雀东南飞》是另一类型的爱情婚姻悲剧。此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长篇民间叙事诗,代表了汉乐府民歌的最高艺术成就。诗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虽是位弃妇,但她不是被丈夫焦仲卿抛弃的,而是被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迫害的,她的丈夫也是同样的牺牲品。她和丈夫婚后感情很好,而焦母容不得她,硬逼着儿子休妻。仲卿不得已,只得暂把她送回娘家,以待时机再接回来。不料她回娘家后,太守便派媒人为子求婚,刘兄贪图财势,逼她改嫁。她在与仲卿最后相见时,约定同死。结果她投水自杀,仲卿上吊自尽。全诗正是通过二人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残酷迫害,热情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他们为反抗礼教而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并寄托了人们对他们的同情和战胜封建礼教的愿望。诗歌成功塑造了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刘兰芝的勤劳、善良、美丽、钟情、坚强、刚烈汉乐府民歌,焦仲卿的忠厚、纯洁、深情、由软弱变得坚强,焦母的蛮横无理,刘兄的攀附权贵、唯利是图,都描绘得形神毕现。另外,诗歌精于剪裁,叙事繁简得当,结构完整紧凑,曲折生动,成功运用了比兴和铺陈手法,对话富于个性化。
在表现爱情婚姻题材的叙事作品中,《陌上桑》是与上述作品均不相同的。它通过对罗敷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歌颂她坚贞的品质和不慕权势、敢于反抗的精神,鞭挞了上层人物的荒淫,表达了劳动人民维护自己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凛然正气。全诗充分利用戏剧性冲突,运用夸张、铺陈、虚构等浪漫主义手法,成功地塑造了罗敷这一典型形象,具有很强的喜剧效果。
汉乐府民歌中还有一些寓言诗,善用拟人手法,想象奇特丰富,曲折暴露了统治者的凶残本性,表现了人民忧生惧祸的心理,并留下了一些有益的社会生活经验。如《乌生》告诉人们世情险恶,随时随地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枯鱼过河泣》以枯鱼过河喻世道险恶,告诫人们行事要谨慎。
此外,乐府民歌中还有一篇以劳动为题材的名篇——《江南》,用反复咏唱的形式,描绘鱼儿在莲叶四周戏游的情景,表现了采莲青年男女欢愉的心情,展示了江南水乡明媚秀丽的风光,语言浅朴自然,格调清新明朗,活泼欢快。
总之,汉乐府民歌广泛、深刻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思想感情。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汉乐府民歌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是以叙事为主,善于剪裁和安排情节。汉乐府民歌虽也有一些抒情诗颇具时代特征,但最能体现其特色的还是大量的叙事诗。这些诗有的描写一个场面,有的叙述一个完整曲折的故事,在叙事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中最成熟的作品是《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两诗都注意以人物关系构建叙事情节,以人物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并注意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不同的是,《陌上桑》截取事件发展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横断面作横向展开,以罗敷为中心,所有冲突都围绕罗敷与观者、罗敷与使君的关系产生,在冲突达到高潮时,戛然而止,耐人寻味。《孔雀东南飞》则把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性格、命运建立在更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上,前半部分,将焦、刘的深情厚爱,交织在恶化的婆媳关系和不和谐的母子关系中,从而形成爱情与家长权威的矛盾,冲突以封建家长制的胜利暂告一段。后半部分,波澜又起,县令、太守相继求亲,主簿、郡丞巧言为媒,刘兄趋炎,刘母柔顺,焦母冥顽,进一步左右着人物命运,推动着情节发展,主人公的抗争,终未能逃脱宗法、社会势力以及庸俗社会意识织成的罗网。情节曲折跌宕,结构复线交迭,前所未有。
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刻划人物的性格特征是汉乐府民歌的又一艺术特色。《东门行》中妻子与丈夫的对话,《上山采蘼芜》中弃妇与故夫的答对,《陌上桑》中罗敷回答太守之语,都口吻毕肖,充分表现了人物各自的个性特征。乐府民歌还注意刻划人物动作。如《艳歌行》以男主人公“斜柯西北眄”的动作,来表现其猜疑。《陌上桑》中写“罗敷前致辞”,表现她的从容不迫,勇敢无畏。《孔雀东南飞》中焦母捶床大怒,刘母拊掌而悲,也传神地表达了不同的人物个性。
汉乐府民歌还善于运用比兴、拟人、夸张、铺陈和烘托手法。如《白头吟》以“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比喻女子的爱情纯洁。《乌生》使腐臭的鱼哭泣,《战城南》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让动物具有人的情感,想象奇特。《上邪》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具有浓重的浪漫色彩。《陌上桑》以铺陈手法,通过对罗敷衣着打扮的铺叙,表现了她的美丽;通过对夫婿英俊、事功的铺陈,表现了夫婿的不同凡俗。《十五从军征》以“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句,烘托了老兵家园的破败和他心境的凄凉,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句式上打破《诗经》的四言,以杂言为主,逐渐趋于五言。如《妇病行》、《孤儿行》等篇,用的是杂言,句式灵活,对于协调诗歌节奏,形象地表现人物的神态、语言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有着重要作用。《白头吟》、《陌上桑》等,用的是整齐的五言,便于双音词与单音词的组合,寓变化于整齐之中,扩大了诗歌的容量。一般说来,西汉乐府民歌多杂言,东汉则多五言。杂言体式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五言体式是文人五言诗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