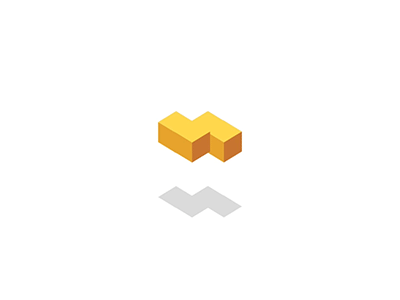文化记忆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表现为身份功能、生产功能和情感功能。 文化记忆为政治合法性和执政稳定提供记忆支持和记忆材料。
#01
文化记忆的意识形态认同功能
文化记忆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为社会成员中的个体提供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第一,文化记忆的认同功能。 “在文化记忆的帮助下,一个集体的成员建立并培养了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在文化记忆的分享与回忆中,集体成员就“我们是谁”、“我们应该记住什么”等问题形成共识。 需要一个共同的过去,而对当下的认知和解读需要通过对过去的回忆来获得。 正因如此,集体成员在相应的文化记忆仪式中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对一些关乎共同体命运的重大问题形成了新的视角。 共识,达成共识,共同行动。
第二,文化记忆的政治认同功能。 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中,文化记忆也会为政治统治服务,成为强化政治合法性和政治认同的重要工具。 正如有学者指出:“一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文化规范和社会禁忌,往往决定性地塑造着社会记忆的框架。” 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决定了文化记忆的解释框架和功能体系。 文化记忆被特定媒介铭刻、传承和唤醒的过程,也是被重构的过程。 一些具有政治属性和意义的文化记忆,将在被唤醒、重构和赋予意义中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以纪念碑、纪念馆和图书馆为例,正如阿莱达所指出的:“统治者不仅要篡夺过去,也是为了未来,他们希望被人记住,所以他们为自己的行为立碑。” “记忆场”承担了一个特定的回忆任务,当人们身处其中时,他们的注意力会转移到替代符号和特定的符号系统上,而这些政治符号、政治符号和政治意义正好可以为政治合法性提供辅助,并且对历史的记忆共识转化为政治共识和政治认同,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结构下完成的政治认同也将为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助力。
#02
文化记忆的意识形态生产功能
文化记忆还为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储存的知识和记忆材料。
首先,文化记忆为意识形态生产提供了知识储备。 文化记忆具有储存知识的功能,特别是通过文字媒介保存和传承的文化记忆,将一定的知识以符号的形式具体化和固定化。 “文化记忆包含了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不可或缺的表现。文字、图片、仪式的知识体系。” 这种知识体系不仅帮助人们认识自我、解释世界,而且成为一定时代意识形态生产和再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知识储备。 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已故祖先的传统像噩梦一样萦绕在生者的脑海中。” 马克思虽然没有指出文化记忆的概念,但马克思的论述中包含了对文化记忆功能的书写文化记忆难道不是像噩梦一样萦绕在活着的人们的脑海中吗? 它继承了祖先的智慧和知识。 当现实需要时,它就会被唤醒和激活,成为思想生产的重要依据。 同样,恩格斯也认为,应该以现有的知识和材料作为思想和概念产生的基础。 进一步处理。” 文化记忆可以为意识形态生产提供现成的材料和知识储备,无论是功能性记忆还是储存性记忆,都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生产的基础材料。
其次,文化记忆为思想叙事提供了丰富的记忆素材。 一般来说,在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中文化的功能,会采用多种叙事方式来增强传播效果,而多元叙事必须有丰富的常识性知识和概念材料作为支撑。 作为社会成员共同历史的见证、记忆的呈现和过去的表达,文化记忆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储存着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供意识形态生产者提取和整理。 以最基本的讲故事为例,文化记忆本身就是一个储存故事的熔炉。 历史故事借助文化记忆被社会成员回忆起来,并在文化记忆中被各个时代的人们诠释解读,进而被赋予新的意义。 意识形态隐喻、符号和意义。 当意识形态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时,文化记忆可以为其提供丰富的历史事件和故事模板。 同样,意识形态在采用文本叙事时,需要明确表达“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等基本问题,而文化记忆就是记录一个国家,它在哪里?一个民族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在文本叙事中,既要依靠文化记忆将这些问题交代清楚,同时又要将叙事中的政治合法性等问题交代清楚,以达到特定的意识形态目的。 当意识形态采用图像叙事时,图像媒介所储存和传承的文化记忆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视觉素材。 “图像在人类记忆中起到了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在这个中继站中,它们会被充电,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意义会被倒转,也就是能量会被倒转。” 也就是说,图像记忆不仅可以储存人的情感能量,还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释放新的能量,产生新的能量,而且能量的方向还是可以改变的。 当它用于意识形态生产时,它所储存的情感能量将被用来宣扬特定的意识形态认同。
#03
文化记忆的思想情感功能
在阿斯曼等人的论述中,文化记忆不仅具有记忆的功能,还具有情感的功能。 一旦这种情感被政治权力所掌握,文化记忆就会发挥意识形态情感的作用。
首先文化的功能,创伤记忆为意识形态认同提供了巨大的情感能量。 借用瓦尔堡的话,阿雷达将创伤性文化记忆称为“苦难的宝藏”,它以经验的形式进入集体无意识领域,“它们构成社会记忆的母体或持久痕迹,会在变化的历史情境下再次激活”。 这种文化记忆是一种能量转换器,蕴含着强大而巨大的能量。 当在特定的场景或情境(比如有创伤的地方)被激活时,会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并且这些能量可以被导向不同的方向。 方向,或积极的意义建构,或消极的意义冲突。 对于政治权力而言,这种情感能量可以被引导到积极的建设性方向,转化为意识形态认同的积极力量,并以符号、隐喻、赋予意义的形式,将创伤性文化记忆中蕴含的能量储备引导到权力所期待的方向转化为凝聚共识、巩固认同的能量,进而实现特定的意识形态目标。
其次,文化记忆的“记忆场”为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提供空间场和符号仪式支撑。 “记忆场”是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提出的概念,与阿斯曼提出的“记忆场所”概念类似,主要指集体成员共享记忆的空间。 一方面,场所本身可以成为记忆的主体或载体,如破败的建筑废墟; 另一方面,该场所为社会成员提供了空间场域和象征性的纪念仪式,例如纪念馆。 对于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文化记忆的“记忆场”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情感体验、情感分享和情感表达的场所。 在集体参与的记忆中,人们的情感能量会在瞬间积累起来。 爆发和分享。 在这种强烈的情感体验中,文化记忆通过仪式、图像、文字、话语等方式呈现和表达,主导这种情感分享和体验活动的当权者,会通过情感叙事来认同意识形态。很短的时间。 建立强大的情感能量。 这种情感功能的实现并不直接依赖于文化记忆本身的内容,而是通过记忆场的塑造、社会成员的身体参与、相关仪式的举行,为意识形态认同提供情感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