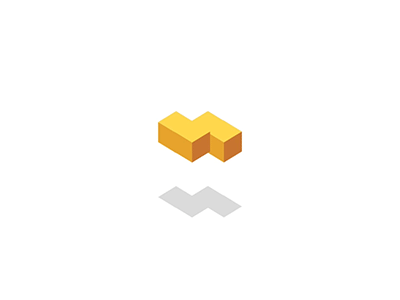论辩双方,周保松,左翼自由主义者,师从石元康先生,对罗尔斯素有研究,现任教于港中文大学,著有《政治哲学对话录》《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在乎》《政治的道德: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小王子的领悟》等。
我讲旧常识,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师从戴晖教授,博士论文为《功利主义中的偏见与利己问题研究》罗尔斯正义论两个原则,代表作有、等。此外,还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武侠小说,题为《武林的黄昏》。
一、周保松
这是我今天寫给一门本科政治哲学课同学的问题,讨论的是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放在这里给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各位,下星期上课前,我再多提几个问题给大家思考。
1,Rawls说,他的主要的理论对手是效益主义,因此他的两条原则及其证成,以及其背后的结构,都和效益主义针锋相对。通过这个比较,我们就更能看出他的理论的特点。
大家因此需要思考:它们两者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异,例如一个是目的论(teleological),另一个是义务论(deontological);一个是“good”优先于”right”,另一个是”right” 优先于”good”;一个重视个体的独立与分离,另一个则是将所有人溶入一个想像中的大我。(大家宜细读A Theory of Justice, section 6)
2,Rawls说,平等公民的基本自由,是正义社会的首要原则,同时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例如不可以诉诸社会整体利益来牺牲个人权利)。在这个基本自由的清单中,政治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是重中之重。
问题是:平等的个人基本自由,为什么是正义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时为什么可以享有这样绝对的优先性?他到底诉诸什么道德理由,论证基本自由的优先性?
这是理解Rawls 理论的一个大关键。他在《正义论》修订版中对这个问题题的论证,和初版有很大不同。重覆一次问题:基本自由对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要?
3,Rawls说他要重新回到John Locke, Rousseau, Kant的社会契约论传统(留意:他没有提Hobbes)去证成他的原则。所以,他的Original Position就相当于State of Nature,尽管他的目标和Locke,Kant完全不一样,他的目标是要证成一组正义原则,而不是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他在书中也清楚指出,他的契约论是假设性的(hypothetical),只是一个思想实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既然如此,他的契约论的性质是什么?契约在什么意义上起到证成(justification)的作用?无知之幕下立约者的“同意”,其实是什么性质的同意?
大家好好想想这几个问题,星期二我们继续讨论。(其实答案大都可在印给大家的TJ, Sections 1-6中找得到。)

二、我讲旧常识
功利主义并不需要把诸个体融入想象中的 “大我”,首先,诸独立个体也能(且最终只能)凭共情能力获知他人的幸福和痛苦;其次,任何道德哲学都是诸独立主体之间的道德,这是道德的语法,既不存在 “个人道德”,也无所谓 “集体大我”。
罗尔斯的另一个问题是:他说功利主义是good优先于right,这样说则忽视了功利主义内藏的语言批判维度,早在边沁的文本中就有很多语言批判的成分。功利主义完全可以说right实是语言虚构,此种幻觉的实质仅是根据人的某些生活形式(例如人是有语言的动物)为 “长久善” 设计出的制度。
三、周保松
謝謝你的回覆。你的問題比較重要和複雜,很難用一百多字回應,我試試另開一個貼子解釋一下我的觀點。
(新帖)對效益主義的一些解釋和回應
//我讲旧常识:功利主义并不需要把诸个体融入想象中的 “大我”,首先,诸独立个体也能(且最终只能)凭共情能力获知他人的幸福和痛苦;其次,任何道德哲学都是诸独立主体之间的道德,这是道德的语法,既不存在 “个人道德”,也无所谓 “集体大我”。//
有朋友在我昨天贴出来的关于罗尔斯的贴子中,作了以上留言。我觉得问题很好也很重要,故另开一贴作一点回应和解释。
1,首先,“功利主义”的英文是Utilitarianism。我一向认为这个翻译会容易带来误解,因为utilitarianism是一种利他主义式的理论,在有必要时会要求个体为了社会整体快乐和福祉而牺牲个人利益。中文的“功利”一词,多少带点贬义,有种凡事讲实际算利益的自利主义的意味。所以,我主张译为“效益主义”(也有人译为“效用主义”)会好一点。
2,回到第一个问题:“功利主义并不需要把诸个体融入想象中的 “大我”,首先,诸独立个体也能(且最终只能)凭共情能力获知他人的幸福和痛苦”。
就第一个声称,我是同意的罗尔斯正义论两个原则,效益主义是不需要或不必要这样做的——如果它有更合理的解释和证成自身的方式。所以,这种预设某种“想像的大我”的诠释,确实是罗尔斯的观点。例如Will Kymlicka(金里卡)在他的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有中译本)一书中便有很不同的诠释。他认为,效益主义的道德目标,其实是要体现和实践一种“平等主义”的理想。哪一种诠释更合理,我这里暂时按下,但最少我们知道是可以有不同的论证进路的。
3,不过,作者在第二句却提及,“诸独立个体也能(且最终只能)凭共情能力获知他人的幸福和痛苦。”这即表示,作者也同意,在效益极大化过程中,作为独立个体,如果他要实践效益原则的要求——即“在一个特定处境下,当且仅当一个行为能极大化所有受影响的人的效益时,该行为才是道德上对的”——那么他必须要有一种共情能力(empathy or sympathy),他才有足够的道德动力去这样做。
问题却在于:如果他是一个独立个体,有着自己的利益和人生计划,为什么他会愿意随时放下自己的根本利益去服从效益原则的要求?對他人的共情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和優先性?
这个一方面是能不能的问题,即道德心理上是否过于苛求(too much demanding),另一方面是道德上是否可取(desirable),因为它要求的共情及消极责任很可能會扭曲人的生命的完整性,并吞噬人的一些重要的理想和规划。(这个讨论可以参考Bernard Williams在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中的精彩讨论。有中译本。这里我暂时不多谈。)
那么效益主义可以如何為自己辩护?
一个可能回应是:当我们考虑道德问题时,不要视自己为完全独立的个体,而应视自己和所有人活在一个「道德大我」之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大我的一部份,所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便不是一种迫不得已我牺牲,而是为了更好的社会整体利益而作出的自願努力,就像一个人平时会很乐意为了更长远的利益而牺牲当下的个人享乐一样。
当每个效益主义者都有了这种大我想像,“共情”的正当性和优先性,才比较容易理解和证成。在此意义上,效益主义传统,确实是有这样一种“大我”想像。(強調多一次,這不是唯一的進路,雖然我認為這是很合理的一種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