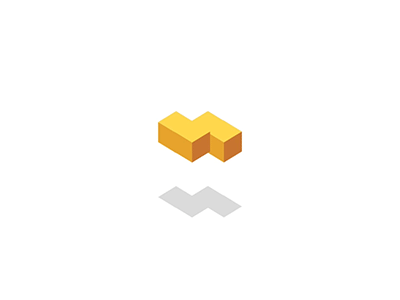千年前,曹植写出了《洛神赋》,这原本只是”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但由于自东晋以后,《洛神赋》也成为流行的书画题材,画家及观众的视角,使得对它的解读发生了改变。同时由于甄后之死,在魏明帝时代就是颇受关注的话题,融入很多想象,再与《洛神赋图》结合,便为《洛神赋》增添了传奇色彩,既赋予它”感甄”的内涵,也创造出一段爱的历史。
一、“洛神赋”的来源
曹植的《洛神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他以对话的方式,讲述第一人称的”余”(君王)离京返国,途经洛河时,与洛河之神宓妃的一场邂逅。《洛神赋》在南朝时便得到很高评价,后来更成为曹植最有名的一篇作品,而洛神也以女神或女性的形象在社会中家喻户晓。由于这样深刻的国民度,在往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洛神不但经常出现在诗词歌赋、小说戏曲等文学体裁中,也出现在其他艺术门类,比如传统的绘画书法,甚至到了现代,也同样活跃在戏剧电影中。
不得不说,洛神的故事,流传了千年,却总是能够以新的面貌再次吸引大众的注意,堪称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而这样的经典作品,必然引来无穷无尽的关注和解读,其中最让人疑惑的便是这篇赋的命意。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雍丘王曹植奉命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朝拜京都。曹植满心喜悦,然而,当他抵达洛阳后,才发现事与愿违,到处碰壁。在洛阳期间,大雨滂沱,伊洛泛滥,建筑、道路被毁,最出乎意料的,还有曹彰的突然去世,两个月后,剩下他与曹彪返回各自的封国,又被禁止在路上同宿。
这一趟省亲之旅彻底打破了曹植的幻想,他写下《赠白马王彪》的组诗,诉说自己千辛万苦赶到洛阳,不曾想”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因而倍感凄凉。
这一年,曹植三十二岁。此行过后,他写下了《洛神赋》,因此有人说是《洛神赋》是曹植在隐喻君臣大义。但是因为《洛神赋》原名《感甄赋》,甄氏是曹植的嫂嫂,在当时本就是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后来魏明帝将《感甄赋》更名为《洛神赋》,更是引人遐想。
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始终没有定论。因此,本文欲在文学史、艺术史等基础上,结合文学与图像资料,对《洛神赋》作进一步的讨论,重新探讨《洛神赋》的所谓”寓意”,以及这一”寓意”在阅读史中的演变。
二、洛神前传:宓妃与神女
在《洛神赋序》中,曹植写道:”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洛神赋作者是谁,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通过这句话,曹植说明了《洛神赋》的两个灵感来源:一个是传说中的洛河之神,一个是宋玉诗赋中的神女故事。
汉代以来,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洛河之神为宓妃。但”宓妃”的这个人物,其实很早就出现在了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屈原在《离骚》里就写到过宓妃——伏羲之女。《离骚》以后,宓妃经常出现在汉代作品里。比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宓妃在这里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女性,她代表的是天子的无边权力。其后,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也写到宓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扬雄的《羽猎赋》确定了宓妃是属于洛水的。但是到了东汉,宓妃才成了公认的洛河之神。东汉以洛阳为都,除了在自然环境上有优势,还需要得到神灵的庇护,文学家们在创作中便直接将与洛水密切关联的宓妃确定洛水之神,同时也是洛阳的护佑之神。
而”神女”的形象特征被赋予的宓妃身上,源于刘向模仿屈原的《九歌》写作《九叹》,其中宓妃成为了清明廉洁的政治的象征,而这原是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中,”神女”所代表的含义。《高唐赋》写的是宋玉与楚襄王游于云梦之台,面向高唐之观,宋玉对襄王说起从前楚怀王游高唐的故事:楚怀王困倦而昼寝,梦见巫山之女”愿荐枕席,王因而幸之”,其后为之立庙,号为”朝云”,赋的很大篇幅是在描写高唐的自然环境,而神女只是国家昌盛的象征。
神女
楚襄王听了宋玉之赋高唐,梦中恍惚遇见神女,于是便令宋玉写下《神女赋》。《神女赋》的相当大篇幅也是在描绘神女,写神女的样态、行止,写神女与楚襄王的交往。
这是一个美丽、富态的神女,她的面庞温润如玉,她的五官精致,她的气质优雅,她的举止大方,她的步态雍容。
在神女与楚襄王的会见中,起初是神女若有所动,随之彷徨不定,然后,由于双方互表爱慕,”精交接以来往兮”,襄王”心凯康以乐欢”,却不料神女突然变卦,”摇佩饰,鸣玉鸾,整衣服,敛容颜,顾女师,命太傅,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而楚襄王挽留无效,独自”回肠伤气,颠倒失据”,”惆怅垂涕,求之至曙”。
《神女赋》中楚襄王与神女的相会一波三折,楚襄王对神女的欲望,与这种欲望相对照的神女的喜怒无常、无从把握,都被作者刻画得丝丝入扣。就楚襄王而言,神女的诱惑无法抵挡,可是神女又终归”不可乎犯干”,欲罢不能,却又求之不得。
以”神女”为唯一的主角,将笔墨全部倾注在神女身上,这一点是《神女赋》独有的,而这《洛神赋》的写成很有影响。特别是《神女赋》说楚襄王不能够如愿与神女结合,最大的障碍,在于他们之间”交希恩殊”,也就是人神阻隔,由此,神女在关键时刻毁约,令楚襄王不知所措,所以,”神独亨而未结兮,魂茕茕以无端”。”交希恩殊”,在《洛神赋》里,便是”人神之道殊”。在这一点上,《神女赋》也影响了《洛神赋》的故事结构。
楚襄王
综上可知,《洛神赋》借助了宓妃的传闻与神女的文学书写,最终创造出文学上的洛神形象。
三、 洛神赋图:画家的再创造
晋宋以来,《洛神赋》深受欢迎,一方面是为诗赋作家所效仿,另一方面,是成为一些绘画、书法作品的素材。
最早以《洛神赋》为摹本,进行文学创作的是谢灵运洛神赋作者是谁,在他的《江妃赋》中,江妃的容貌姿态和情感表达,都有《洛神赋》的影子。其后,江淹的《水上神女赋》明显继承了《洛神赋》的叙述模式,还有另外一篇《丹砂可学赋》,用了《洛神赋》的典故。南朝时喜爱《洛神赋》的作家很多。据洪顺隆说,江淹的《丽色赋》、沈约的《丽人赋》和《伤美人赋》、袁伯文的《美人赋》也都是《洛神赋》的投射。此外,不独萧统在《文选》卷十九”情赋”的类目下收入《洛神赋》,萧统的父亲梁武帝萧衍对王羲之法书中的《洛神赋》也有很高评价。
谢灵运
扬雄曾说作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文心雕龙·诠赋》也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都是讲赋有排比铺陈、状物如绘的特点。汉魏赋作家而又擅长绘画的人,似乎也很不少。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张衡就是”善画”之人,能用脚画动物,蔡邕也”工书画”,能画人像,传说汉灵帝诏令他为赤泉侯杨喜一家五代将相画像,他又画又写,号称画、赞、书”三美”。
曹植是否能画,尚未见有文献记载,但他作过《画赞》,基本上是以文字形式来说明画面,或者补充未能形诸画面的内容,可见,他对绘画有着深切的了解,而他的诗赋也具有较高的画面表现。
汉代以来,文人越来越多的在文学与绘画两方面都进行了参与,导致两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作家可以依据画作写出诗赋,而画家也可以根据歌诗辞赋做出画作。
从《历代名画记》的记载,可以知道依照《洛神赋》绘制《洛神赋图》,最早的一位作者,便是晋明帝司马绍。尽管晋明帝的《洛神赋图》早已亡佚,今天所传署名顾恺之作的《洛神赋图》也被证明都是宋人的摹本,是12世纪古老想象与当代奇想的结合,但是,丘巨源《咏七宝扇》诗中的”画作景山树,图为河洛神”,仍可证明南朝时确有以《诗经》、《洛神赋》为主题的画作,而从它们的绘为扇面来看,《洛神赋图》很有可能还与《诗经图》一样为世人所喜爱。
《洛神赋图》局部
顾恺之是卫协的弟子,有”三绝”,即才绝、画绝、痴绝之名。《晋书》本传说他”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他的画在当时就很珍贵,传说他”曾以一厨画寄桓玄,皆其绝者,深所珍惜,悉糊题其前。桓乃发厨后取之,好加理。后恺之见封题如初,而画并不存,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还有传说,讲他”为人画扇,作嵇阮而都不点睛。送还,主问之,顾答曰:'那可点睛,点睛便语。'”
这种重神气、略形迹的画法,在中国人物画史上是一个极大的贡献,在当时则颇能迎合崇尚”无”的思潮、趣味,所以,后人将《洛神赋图》归在这位大名鼎鼎的画家名下,是有意借重他的名声和地位,更何况,如《历代名画记》所记载,他也确实根据曹植的诗作过画。当东晋南朝,《洛神赋》作为文学经典而被称赞、被效仿的时候,画家也视它为绘画的素材。但尽管赋本身就有绘画的特性,曹植也属懂画之人,然而《洛神赋》毕竟是文字,不是图像。绘画转写文字之赋,与单纯的文学模拟因此又不相同。
那么画家眼里的《洛神赋》究竟如何?这里以同为宋人模拟南朝本的故宫绢本《洛神赋图》为例。
第一,在整个画卷中,洛神大多是在水里,而帝王几乎都在陆地的,”人神之道殊”,一望可见,其间,洛神两度登岸,与帝王相对,是为人神之交流。陆地与河流,是这长卷不断变换的两个场景,它们的交替出现,不仅呼应着《洛神赋》的主题,叙述了帝王邂逅洛神,却又得而复失的经过,也使整个画卷富于变化和节奏。
第二,对洛神形貌举止的描写,在《洛神赋》中占有较大篇幅,这是文字不得已的地方,而到了《洛神赋图》里,那些经过翻来覆去、重重叠叠文字描写的内容,只需要一个固定空间、一个简单平面即可展示。但相反的是,在《洛神赋》里作为叙述文字、一笔带过的”余”(君王)的活动和心理,形诸图画,也不得不占有相应的空间和篇幅,于是,君王的身形与洛神相仿佛,君王形象在画卷中的鲜明、突出,达到了与洛神平分秋色的程度。这一点,图与赋有很大不同。
第三,在《洛神赋》转写为《洛神赋图》的过程中,原来赋里只有一个主角洛神,发展到图里,变成了洛神和”余”(君王)两个。因为赋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叙述者”余”可闻不可见、隐身而无形,然而,图要表达《洛神赋》所讲述”余”和洛神的关系,就不能不将”余”形诸图像,使叙述者的”余”由隐而显,由无形而有形。
《洛神赋图》局部
由此可见,尽管《洛神赋图》取材并且忠实于《洛神赋》,可画家依然有他的”第三只眼”,从事所谓”二度创作”。画家不但能依靠文字描绘出洛神的形象,也能在没有文字依傍的情况下,描绘出创造了洛神的赋作家,并使赋作家与他书写的对象,出现在同一时空里、同一画面上。从《洛神赋》到《洛神赋图》,就这样,”她”和”余”的故事,变成了”她”和”他”的故事。
四、甄氏与曹植,构造的历史
当绘画把《洛神赋》变成”可见的形象”之后,赋这一文学体裁本来唤起形象的功能,自然被绘画所取代,这势必影响到《洛神赋》的传播。到了唐代,一方面由于诗赋取士的需要,《文选》成为士人举子必读的诗文范本,可以想见,《洛神赋》也得以借此流传,可是另一方面,种种与历史相关的传闻附会于《洛神赋》,又赋予其新的传奇色彩。《文选》李善注胡克家重雕尤袤本所引《记》一则,便是有趣的例子。
在李善注胡刻本《洛神赋》时,他说:
“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在此李善通过《洛神赋》,将曹植与甄氏联系在一起,也将《洛神赋》写作内涵定为两人爱情。
这个例子带出的信息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将作者曹植对号入座,变成《洛神赋》里的”君王”,确认了赋中第一人称的”余”便是作者本人的事实。这可以看作是,在《洛神赋图》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画家特有的观望方式,也就是把赋作者及其书写对象放在同一画面上的叙述方式,出现在了对《洛神赋》文字的解读当中。与此同时,这一则传闻又将洛神比附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曹丕的夫人甄氏,并为此制造出甄氏与曹植的一段恋情。
据陈寿《三国志》记载,甄氏家世吏二千石,其父甄逸为上蔡令。汉末建安中,她先是嫁给袁绍之子袁熙,建安九年,曹操攻占邺城,她又被许配给曹丕。后来,曹丕继承曹操的权力,并建立魏,成为魏文帝,助他谋取大位的郭氏也备受宠爱。甄氏因此有了怨言,文帝非常气愤,于是赐死了她,葬于邺城,并且立郭氏为皇后。但曹丕在位不过七年,曹叡对母亲却是始终不能忘怀,在他即位为明帝后的十余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举办各种悼念仪式、追思活动,令甄氏一直活在人们记忆之中。
在这种氛围里,有关甄氏、特别是她冤死的传闻不断发酵,还夹杂着对曹丕的谴责的声音。曹植与曹丕之间这种政治对手的”相煎何太急”的关系,在当时及日后都是被热议的话题,加上传说中甄氏与曹丕的恩恩怨怨,曹植、甄氏两个政治上同样被”牺牲”的人物,两个在与曹丕的关系中同样的弱势之人,自然而然被归到一起,并被演义出共患难式的恋情。
就这样,曹植、甄氏的故事不断被再创造,到了如今,在现代人眼里,《洛神赋》讲述的就是曹植与甄氏恋爱的故事。而在现代艺术史家的叙述里,《洛神赋图》也几乎是被当成洛神与曹植的邂逅图,画卷中”君王”的形象,往往都用”曹植”或”陈思王”来称呼。
结语: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自从《洛神赋》被创作出后,在历史的流转中,由于文学和绘画形式的再创造,它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甚至对曾经的历史叙述有了极大的影响,而这是由中国文学和文化独有的环境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