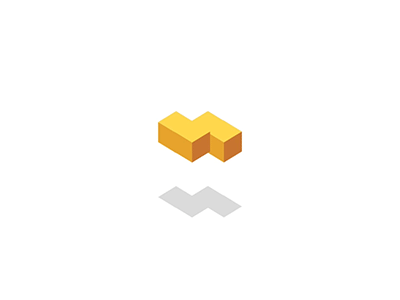前言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的关系开启了全新的历史进程。《史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诸侯间争相发展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意图成为强国称霸一方,吴越相争便是其中的关键一幕。
范蠡与西施都诞生于春秋时期吴越相争的政治背景之下,在先秦古籍中有一些著作分别记载了二人的生平及形象特点。
一、对西施:分散记述其形貌之美
与范蠡相比,有关西施的记述多散见于诸子著作之中,且篇幅较少,如《墨子·亲士》中就已经有了“西施之沉,其美也”的说法,这就表明了西施的结局为沉江而死。另外《庄子》中也有相关记述,由此可见,在先秦典籍之中,范蠡与西施都已是为众所知的人物,一个以智囊团的身份闻名遐迩,一个以其貌美多姿而受到关注,但二人却并无交集,都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进行描写记述的。这也是本文进行后续研究的历史基础。
范蠡与西施的真实结局在中国文化中,利用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创作出的多彩故事举不胜举,在这些故事之中,人们对于主角寄予褒奖或贬斥的评价,主角的形象依托主观创作而塑造,个体的思想感情也因此得到了表达宣泄。
从上文所列举先秦时期部分作品的记载来看,范蠡与西施终是并无交集。有关二人的真正结局,在吴越争霸前,《墨子·亲士》篇就写过“西施之沉,其美也”,因为实在貌美,曾使得人心惑乱,或因为怕其惑乱人心,结果被沉入江河里。可见在先秦文献中的记述,西施的结局是沉江而死。
范蠡西施二人首次同时出现在同一部著作中,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赵晔所著《吴越春秋》和袁康所著《越绝书》中,二书开始对人物进行文学性的书写,将其置于吴越相争的宏大背景当中。范蠡和西施也就由此开启了由历史人物向文学形象的转变。
范蠡保留了史籍记载里的政客身份,在帮助勾践一雪前耻后飘然远遁,西施则成为越国复国大计中的重要一环,作为政治工具进献给夫差以行魅惑之举,但范西之间仅有国家利益的纠葛,政治上联系紧密,与爱情关联不大。《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具有“小说家言”的性质,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言,小说是出自稗官野闻街谈巷语,经过口口相传中不断润色而形成的。由此可以推断,由于作者把苎萝山鬻薪之女放在吴越相争的政治背景下,以舍身报国的形象引出,加之后世作者对其人生经历不断渲染发挥,她的故事与形象就愈发深入人心,而人们出于对美之凋零的同情,便不忍“越女西施”有此沉江的悲惨结局。
虽然这两部著作现仅存残本,流传下来的部分均未写明二人的最后归宿,但通过后世作品中征引的《吴越春秋》与《越绝书》原文,得以一窥当时的结局归宿。如晚唐陆广微的《吴地记》引《越绝书》:“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另有北齐祖珽《修文御览》引《吴越春秋》:“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从所引文献记载中均可以看出,《吴越春秋》与《越绝书》对二人结局的不同书写,实质已经成为之后范西故事结局分化的最初源头。
到唐代,经过前朝的艺术加工及流变演绎,在这一时期范西二人的艺术形象已经开始深入民心,晚唐陆广微《吴地记》记载:嘉兴县县南一百里有语儿亭,有关诗词题材中的范蠡西施故事,唐代主要以分散描绘为主,范蠡与西施多单独存在于诗词作品中,著名诗词大家譬如李白、王建、元稹等人,常借助范蠡和西施的意象,或施以功过评价,或寄寓怀古之情,作品数量相当丰富。
二、范蠡、西施的情感经历
《浣纱记》第二出《游春》中,描述了范蠡与西施相遇定情之经过。在这一出里,生、旦先后出场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范蠡字少伯,楚国三户部落人,深谙权谋之术,擅长用兵之道;西施本名施夷光,世代居于苎萝山以浣纱为业,因家境贫寒、所居偏僻,所以即便有不凡美貌也不为世人所知,至今仍未婚配。
范蠡在若耶溪这个地方游春时与西施初遇,西施的美貌深深吸引了他,文中写范蠡评价西施为“采药之仙姝”“避世之毛女”《浣纱记》也描绘了二人定情、分离、重逢、再分离、再重逢的波折过程。在二人两情相悦私定终身后,范蠡回归朝廷,继续发挥其谋臣作用,西施则继续居于若耶溪浣纱为生,在定情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吴越战火燃起,越国战败,文种贿太宰,范蠡陪同勾践入吴为奴,吴王放归勾践,卧薪尝胆密谋复国因战乱导致的波折使得范蠡与西施一直没有再见,他们二人的下一次重逢,是在勾践定下美人计命范蠡寻访美女之时。
范蠡与西施的重逢并未代表二人故事的美好结局。吴王好色,进献美女,从中取事,国家兴亡,全在此举。范蠡身负寻访使命,而西施生性聪明,容颜绝世,是献吴的最佳人选,因此范蠡做出了割舍爱情的决定,希望西施能与他一道同心为国。西施内心无法割舍充满苦痛,但若不行救国之举,国破家亡,与范蠡也再无百年只好,因此西施答应入吴。在《别施》一出中,范蠡将西施带回越王面前,越王安排专人教习歌舞,到献吴之时,勾践夫妇亲扶西施上车,为其送行,而后范蠡、西施二人互诉衷肠,范蠡再三嘱咐西施一切小心在意,以国家为重,计成之后必有归来的日子。临别前,西施将范蠡所赠溪纱一分为二,各自保存,以表忠贞不渝之情。这是二人的再分离。
三、、范蠡与西施的爱情特色
梁辰鱼用较为平实的笔墨书写了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没有大量词藻的铺叙,也没有过多地纠结于主人公之间的儿女情长,更多着墨于家国背景下爱情的厚重感与人物行为的被动性。范蠡与西施的爱情在此没有封建家长的阻挠,而是将阻碍二人的因素设定为更大层面的国家利益,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二人为拯救国家被迫放弃爱情,但结局又获得团圆,其中既有波澜壮阔的大爱,又有深情不渝的小爱,相比传统意义上描写才子佳人的爱情小说,更具主题与情怀上的高度。
第四十五出《泛湖》中,扮演范蠡角色的生角唱道:人生聚散皆如此,莫论兴和废。富贵似浮云,世事如儿戏。由此可知,梁辰鱼所作《浣纱记》中,范蠡西施的羁绊是串联历史与国运的重要一环,并非只是单纯地展示一个爱情故事范蠡西施,在而是在其中寄寓历史兴亡之感。在这一情节中,范蠡晓之以理用社稷存亡说服西施答应入吴,屈志辱身;另一次是美人计的成功实施导致吴国灭亡后,他担心西施留越会使勾践被魅惑,遂将西施带走,共同归隐五湖。
从范蠡的作为与选择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施的感情更多让位于家国责任,一旦面临个人情感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他会无条件选择国家而牺牲个人情感,即使在结尾有作者所安排的形式上的好结局,但也经过了理性思考,是为了国家而与西施远遁的。与之相反,西施在整个故事中所展示出的,是一个对待爱情十分纯粹的形象,她的很多选择虽有不愿,但也受到了自身对范蠡感情的影响,即使范蠡单方面选择暂弃二人情感,她也始终不改痴心。因而,《浣纱记》中的范蠡与西施,并不是站在平等的爱情立场上进行活动的,一方是自始至终的痴情守候,另一方是面对国家兴亡时的薄情选择。
蒋承勇在《感性与理性娱乐与良知——文学“能量”说》中写道:“文学是广义的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它生发于实现与满足欲望的种种幻想,并在愉悦中追寻人性解放的途径与理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在愉悦中让人性获得一种自由,进而让人依恋人生和热爱生命。”
从西施的女性角度而言,她作为四大美女的典型代表,其美貌所带来的想象与衍生本身就为文人提供了较多的书写空间,而当她的命运被置于政治的宏大背景之下,与国家兴亡相关,就使得西施愈加成为文人作家的关注对象。从最初苎萝山下的砍柴民女,加入越国的复仇计划,成为吴王宠妃后致其昏庸最后导致灭国,西施传奇的人生经历就已经超越了许多文人的想象。因此,一个丧失了个体人生主动权的弱女子,被迫成为命运的囚徒受人摆布,她的身上,就被寄予了更多情感因素,她作为一种感性书写的承载体,让文人或施以对其命运的同情和关切,或借其形象抒发个人思想情感。西施形象的流变,就经历了从“人之所美也”的美化,到作品中被贬为“红颜祸国妖女”的妖化,再到《浣纱记》中一言一行皆受到范蠡感情的“驱使”而奴化的发展过程。
西施角色的感性承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士大夫文人的伦理观念。这归根结底范蠡西施,是男性在女子地位低下的男权社会里,对女性生存的一种关注和价值评价。范蠡的功成名就体现了古代男性自我追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这就对人生价值提出了“三不朽”的标准,如果人来世间一遭,不去寻求建功立业,则失去了其意义,故而古人十分推崇个人的奋斗与追求。范蠡其人本非思想界的圣人,也没有不同于常人的才华异能,但却在助越灭吴的过程中建功立业,实现了人生的“不朽”,他的功成名就因此契合了古代男性的自我追求。然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功成名就也带来了功高震主的风险,使他们仿佛置身于悬崖边缘。
范蠡对这种情势有着清醒的认知,所以他在拥有一切之后毅然离去做起了生意,三次散尽家财却仍然日进斗金,被后世誉为“陶朱公”,保全了自己的同时落了个好名声,而文种因为未听范蠡劝阻最后为勾践所不容,赐剑自刎而死。范蠡功成身退之德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色一环。纵观整个文学史对于范蠡的描写,我们极少见到关于其负面评价,即使是在文学僵化较为严重的宋明之初,对范蠡的描写也只是单一化地集中于对他审时度势的前瞻性的颂扬。
古代男性对范蠡的推崇,一者为其建功立业的自我价值,一者为其超然旷达之淡然心态,入世还是出世,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都是人生选择及人生价值,不分高下,儒家与道家的光辉在范蠡身上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因此范蠡的人生成为了古代男性所颂扬并推崇的范本,后世文人对范蠡故事的创作与书写正是意图通过其人其事,来寄托功业俱成、来去潇洒的自我追求。
四、西施的命运起伏反映了封建女性地位发展
四千年前,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重新洗牌,男性逐渐掌握了社会的主要资源,女性由母系社会时受尊敬与崇拜的支配性地位,转化为父系社会对男性的依附性角色。女性地位逐步下降。在长达五千年漫长的男尊女卑社会里,男性对女性提出的各项价值要求及审美评判,其中就体现着男性对于女性操控之欲望,如“女子无才便是德”、“美色误国”、“三从四德”等等。而西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角色之一,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此类价值评判,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命运的差异性描写,就反应了封建社会女性的角色发展。
西施由一个单纯的美人形象开始进入到演绎过程,受魏晋时期神仙思想及盛唐国力强盛带来的繁荣开放观念影响下,对西施故事的描绘更加丰富,且少有批判之语;发展到宋代,程朱理学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极大地禁锢了女性自由,这一时期的西施尽管有着沉鱼之美,也难以拯救其被书写成“祸水误国”的命运,其入吴导致吴灭的经历成为男性推脱责任的借口。
因其导致吴国灭亡而批判其红颜祸水,却又怕其回到越国后使越国重蹈灭国覆辙,无论哪一种结局,都承载了男权社会里主导地位的男性对从属地位的女性的价值要求。后世文人在书写中对其的贬斥或赞美,也是封建礼法教化与个性思潮的动态抗衡。直到元明时期,《浣纱记》等作品肯定了西施入吴的关键作用,这是受社会思潮冲击理学桎梏进程中的思想转变,从而对女性所作出客观性、尊重性的评价,他们开始进一步关注女性的才学智慧,通过对她们命运及性格的刻画书写,肯定女性的社会地位及社会价值。
结语
范蠡与西施故事的后世流传之广,创作之多,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当代时期仍不减其活动,如上世纪50年代京剧大家梅兰芳所演唱的《西施》、60年代曹禺所作的话剧《胆剑篇》等等。范蠡与西施的故事演绎实则是一个从无交集向有交集,从个体描写到整体创作的动态过程,它具有如下特点:作者在个人创作活动中,不仅仅是单独叙事首尾呼应,而是在其中加入虚构过的情节内容,对作品文学性、故事性的要求增强,对人物形象的构建花费更多笔墨,情节更加完整,同时,还寄予个体之思。这就使作品具备了更深刻的文学意义。
范蠡与西施故事的演绎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从男性角度而言,对范蠡政治才能和身退之德的描绘成为了古代男性的理想寄托,从女性角度言,对西施形象的塑造影响了女性的审美评判和文人女性形象的创作;其次,范西故事的书写也奠定了历史人物为原型故事演绎的模式原型。且直至当下,依然影响深远。特别是影视文化作为当下重要消费文化的社会现实下,对正面性的宣扬也有利于人们正确理解艺术创作的价值。